牵牛花/喇叭花/紫蓝/深蓝/淡蓝/浅粉/玫红/枣红/李时珍
牵牛花,有些地区称它喇叭花,而日本人称其为朝颜,记得小时候,经常喜欢在晨光里去采那些开满路边的各色野生牵牛花,层叠倒穿在一种草茎上,好似彩色的小长灯笼。
日渐寒冷的清晨里,经常能见到的花,可能就是牵牛花了。且不说人家的墙头、篱架和阳台,或湿地中的芦苇,便是拆迁工地脏乱的砖瓦石堆,草色萎黄的干旱坡地,古老破旧的屋顶……一些以为不会有花的地方,也常能看到一串串作藤生花的牵牛花,使许多本已有些不堪的所在,多了一种别具情趣的韵致。

矮牵牛花
所见到的牵牛花颜色非常多,早已不是“青花”一种。紫蓝、深蓝、淡蓝、浅粉、玫红、枣红、藕荷、玉白、“三色”……有些还镶嵌着白色的花边。还有一种竟然是极美的淡红,重瓣,带着若有若无的白边,很少见,被视为珍品。其花籽深黄,而不是大多数牵牛花籽的黑色。因不知其名,就学李时珍将牵牛花籽按颜色深浅称为黑白丑的方法,叫她“白丑”。
在古籍中,牵牛花最初便是以花籽入书,见于约1800年前汉朝末年成书的《名医别录》,那是一部秦汉医家陆续汇集起来的3卷本药学著作。
牵牛花以花入诗入文,好像多见于宋朝。诸多宋朝诗人都有以牵牛花为题的诗作,佳句可圈可点。因古代传说中牵牛花对应牵牛星,牵牛花诗常别有一种仙家的神秘之美。如,秦观的“仙衣染得天边碧”,林逋山的“天孙滴下相思泪,长向深秋结此花”……

牵牛花
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成大,其《峨眉山行记》中,以三种花形容奇美绝伦的“娑罗树”花,三种花中,就有牵牛花。
国剧与国画,都是中国的珍贵国粹。民国期间,国剧大师梅兰芳、国画名家齐白石,都对牵牛花情有独钟,牵牛花凝聚了两位著名艺术家的因缘情谊。
梅兰芳非常重视戏剧服饰的配色,认为“中国戏剧的服装道具,基本上是用复杂的彩色构成的”。观赏牵牛花使他得到配色的美学启示,觉得“比在绸缎铺子里拿出五颜六色的零碎绸子来比划要高明得多”。为此他精心种植牵牛花,并育出许多新种,赴日演出还带回日本的牵牛花品种。

日本江户时代的画家铃木其一绘制的牵牛花屏风。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。
在中国画里,牵牛花已是花鸟画的一个常见题材。齐白石便擅画牵牛花,他的“红花墨叶”画法,以洋红蘸胭脂画花,浓淡湿墨画叶,干墨焦墨勾勒藤蔓,别有创意,自成一家。而他画牵牛花,缘起于民国九年秋牵牛花开时节,在梅家与梅兰芳的初次相识,梅家的牵牛花,有“百来种样式”,或娇艳夺目,或淡素清雅,许多花竟大如碗口。他一见倾心,感叹“真是见所未见”。
缀玉轩,梅兰芳的书房。每当牵牛花盛开之时,同好者都在此各出精品观赏,并邀请不养花的友人品评,常是梅家胜出。齐白石总是欣然而至。他的牵牛花画作,很多作于与梅兰芳交往时期。其中一帧牵牛花图,特地题字曰“梅畹华家牵牛花碗大,人谓外人种也,余画此最小者”。
牵牛花看上去挺像是吹奏乐器喇叭,漏斗状的花冠有如喇叭口而宛若丝绢,微长的花管有如喇叭管且莹洁如玉,故而亦称“喇叭花”。她们一般只在早晨日出之前开放,在日本有“朝颜”之称。太阳出来后,牵牛花会渐渐谢去。倘若天气多云或阴,见不到太阳时,花则一直坚持开到中午,甚至下午。
于是想,如果这些美丽精致的小喇叭在吹着人们难以听见的神秘乐章,那极可能是一首唤醒太阳的晨歌。
宋人姜夔的《咏牵牛》,有“满身秋露立多时”的诗句。这些小小的喇叭,确常缀满晶莹的晨露。或许她们在唤醒太阳之前,先要苦苦地唤醒自己,而这露珠,其实是从心中沁出的清泪,所以才仿佛洗过一般清丽无比。
牵牛花
听说,佛家彻悟的境界,即是如人觉醒、如日开朗。这样吹出来的晨歌,一定是清音袅袅,宛转萦回,一如牵牛花纤长旋绕的柔藤。
梅家那独特的牵牛花,今天已无缘见到,据说是特地抑制了缠绕芽的生长而没有藤的,理由是牵牛爬藤会花开甚小,色泽单调。
不过总以为,即使果真如此,牵牛花开得再大、色彩再丰富,如果没有了藤,她的美也会减色许多。不会再因藤的缠结曲伸而显出花的疏密有致,也不会再有那种难得的飘逸飞动之感。
敦煌的飞天,并没有云彩衬托,却依然像是在天上飘飞,是因为她们有飘然飞动的长带,牵牛花的藤,不正像是这样的长飘带么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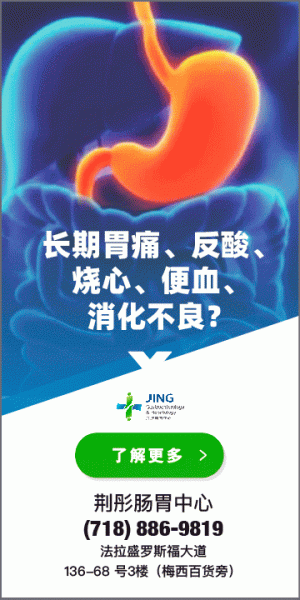
Comments are closed here.